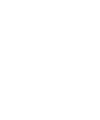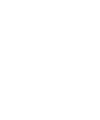引力场(破镜重圆 1v1) - 拾遗(500加更)
这一天沉知周都埋头在资料堆里,过得很充实。
她把近几年所有相关的文献重新过了一遍,每一个技术节点都被仔细标注,可行性分析与风险评估一条条列在表格里。
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数字悄无声息地跳跃着,从四点跳到五点,再到六点。天色由亮转暗,暮色像潮水一般,从窗外一点点漫进来。
一份详尽的回复邮件终于成形。
点击发送后,她利落地关掉了所有窗口,开始收拾桌面。抬起眼时,才发现丁岩烁一反常态地站到了她工位旁,双臂抱在胸前,一副看稀罕物种的神情。
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,沉老师今天居然会‘早退’?”他调侃道,目光在她桌面上扫过,“这阵仗……又准备去‘拾遗’?”
面对丁岩烁的问话,沉知周点点头,把装满的帆布包甩到肩上,“嗯。”
丁岩烁笑了笑,“行,去吧。替我跟老板问个好。”他说完,便重新转回头,注意力又回了那跳动的波形图上。
丁岩烁口中的“拾遗”,是一家开在西门外老街上的书店。年头很久了,久到足以成为几代学子记忆里共同的坐标。老板藏书很刁,口味也好。人文社科类的库存尤其惊人,许多早就绝版的旧书,都能在那儿的某个蒙尘角落里翻出来。也因此,“拾遗”成了学校各类读书会的天然聚集地,一个脱离了网络符码,真正能用实体书籍与在场辩论构筑的精神家园。
沉知周和丁岩烁的第一次正式照面,就是在“拾遗”的读书会上。
彼时她才大一,还是个见了人多场合就犯怵的小姑娘。读书会大多时候是文史哲学生的天下,即便偶尔有理工科的学生光临,也多是出于凑热闹或交朋友的心思。像沉知周这样,每次都来,来了就安安静静坐在角落,认真做笔记,只在被点名时才参与讨论的,确实是个异类。
彼时已是博士生的丁岩烁自然对这个物理系小学妹印象深刻,两个人恰巧又进了同一个实验室,有了这层旧谊打底,关系便天然比旁人近了几分。
只是后来丁岩烁结了婚,读书会那种“杀时间”的青年消遣,便慢慢远离了他的生活。倒是沉知周,始终保留着每个月都要去逛逛的习惯。
少时的沉知周,世界很小,除了物理公式,几乎容不下别的内容。可进了大学之后,尤其是在一帮智识充沛,言谈有趣的同龄人中耳濡目染,那些早就埋下的种子才开始重新破壤,生发出截然不同的新茎。
物理固然是丈量世界运作的尺规,以冷静、克制的逻辑线条,画出宇宙运转的蓝图,解释潮汐的起落与星辰的转动。
但丈量本身,不能取代对世界本身的理解。人性里无法用定理归纳的混沌;那些历史上无法避免的轮回;乃至小说里虚构出的、却比现实更真实的悲欢——这些,都是冰冷公式之外,同样真实庞大的存在。
物理学构筑了世界的骨架,而那些故事,那些纷争,那些不被计入方程的人类情感,是填充其间的血肉。
沉知周走在路上,步履匆匆。
白日里被建筑物切割成锐角的喧嚣,也终于蜷缩进安宁里。对沉知周而言,黄昏与夜晚的交界,是一条无需公式证明的临界线。
线的这一头是秩序,是可计算的已知,而另一头,是属于她自己的混沌。
“拾遗”是她那片混沌里为数不多的安身处。
书店坐落在一条寻常的马路二楼,门也是最普通的那种铁板,并没有太多小资复古情怀,书架挨得极紧,像沙丁鱼罐头,将空间挤压成窄窄的通路,只够一人侧身通过。老板总嫌这地方安静过头没有人气儿,于是常年在外放里,播些很催眠的ECM厂牌的冷爵士。
读书会的人还没到齐,只三两人围坐在最里间的长桌旁,轻声交谈。沉知周向老板点了点头,径直走向角落那个熟悉的位置。那儿靠窗,窗台上总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。无人注意的时候,望出去就能看到街对面小卖部的灯箱。
她刚一坐下,左手边的阴影处便传来一个声音。
“今儿倒穿得像个正常人了。”
说话之人从书架后头的阴影里转出来。年轻女人一身亚麻长裙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。长发随意散着,修长脖颈扮演半路。是那位历史系的女博士,宁嘉。
沉知周早习惯了她这种拆台式的打招呼方式,只淡淡地瞥了对方一眼,点点头,算是答应。
大学里有趣的人很多。宁嘉无疑是其中独树一帜的那位。据说她年纪轻轻,就能徒手将整部《汉书》都疏通一遍,还能边喝高度数的精酿边背诵大段的《诗经》,是人文学圈里有名的青年才女,狂妄与才情等比例地嚣张。
沉知周和她并算不上朋友。只是读书会办得久了,一些熟面孔之间,慢慢沉淀出一种无须刻意维系的默契。
宁嘉也没指望她能作答,注意力很快投向对方手中的平装本。
“看完了?”
“还剩两章。”
“什么感受?”
沉知周翻开书,目光落在自己用红色签字笔画出的重点上。“孔飞力厉害的地方在于,他并没有把‘盛世’看作一个静止的截面,”她说,“整本书都在借一个荒诞的故事,描述一个帝国的官僚系统,是如何在内部的压力下,一步步走向失序的。”
宁嘉探过头,饶有兴致地欣赏她在书上的写写画画。“所以,你相信秩序的自发崩溃?”
今天的讨论主题便是这《叫魂》本书。书里描述了一种奇怪的社会恐慌,流言称有术士可以窃走人的魂魄。这种看似无稽之谈的妖术迷信,如何在乾隆盛世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。
“我不觉得那是‘自发崩溃’,”沉知周摇头,“书中说,所有被指控的人,都只是官僚系统为了向上交代,硬生生‘制造’出来的巫师。真正可怕的,是系统本身为了维持一种'稳定有序'的表象,而不断运转、自我强化,最终制造出更大的失序和恐慌。 。”
沉知周想了想,接着道,“这种‘秩序’本身就是脆弱的。当一个系统不够开放和强壮,任何一点随机的'扰动',比如一句简单的流言,就可能让它滑入混沌理论里所说的'蝴蝶效应 ',在一次次毫无逻辑的迭代里彻底奔向衰败 。”
宁嘉双手托着下巴, 目光灼灼看着她,“用混沌理论拆解乾隆盛世,真有物理系极简主义的美感。”
她略一停顿,又开口:“不过, 你有没有思考过另一个可能性?那所谓的 ‘秩序’,会不会本身就是恐惧最完美的伪装?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就是,”宁嘉笑了,“恐惧'权力被威胁',所以乾隆选择将人民变为符号。恐惧 ‘秩序之外的异类',所以官僚会毫不犹豫抹去所有不听命令的个体,哪怕他是冤枉的。”
她的目光在沉知周脸上停了片刻,随即化为一声轻叹。
“那么我们呢?我们对什么怀有恐惧?我们又在维持着怎样的秩序?”
这个问题轻轻地落在空气里。不远处,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站起身,拍了拍手。
“好了各位,时间差不多了,我们今天的讨论正式开始吧。”“各位,人差不多到齐了,那我们准备开始吧。”
讨论在昏黄灯火里展开。
大家边吃边聊,一如既往的热烈。从官僚体制的僵化,聊到现代社会的信息茧房;从群体的非理性恐慌,辩论到个体自由意志的边界。沉知周大多数时间认真听着,偶尔也参与其中。
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,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工具与思维模型,反复地对同一个文本进行切片与解读。这是一个庖丁解牛的过程,快乐且迷人。散场时已经快九点。
沉知周走出书店时,外头落起了细雨。
湿冷空气让她从方才高强度的大脑激荡中清醒过来。她撑开伞,独自一人慢慢顺着马路往家的方向走。
路面被雨水浸润,反射出路灯昏黄而破碎的光晕。四周很静,只有雨滴砸在伞面上的声音。
记忆中京市是不怎么下雨的,申城才拥有雨季。
在那些被雨水笼罩的夏天,秩序、恐惧、未来这些庞大的词汇,都还没来得及在她的人生词典里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。
一切都还很轻,心也悬浮在半空。下坠的过程,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是哪件不起眼的小事,充当了最初的那只蝴蝶?
走到楼下,来避雨的流浪猫亲昵地绕在她腿前来回蹭。
那只猫大概很懂察言观色,见她没带任何食物来,蹭了几圈觉得无趣,就一扭身子,蹿进了更深的夜色里,连句敷衍的喵呜都懒得给。
沉知周收回目光,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同病相怜。
钥匙插进锁孔,转动,开灯。
客暖黄色的光线铺满了小小的空间。玄关的柜子上,还摆着上次离开时穿的拖鞋,杯子里的水剩了半杯,沙发上的靠垫歪在一边。
一如往常,一切都维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。
可她却不大适应。
回想起来,这几日因为各种原因,晚上她都和江寻待在一起,突然之间,这空无一人的房间就显得过于安静。
屋子里有过第二个人的气息和痕迹,再让他完全退场,竟是这样困难的一件事。
她将帆布包随手扔在沙发上,掏出手机。
屏幕亮起,三条未读消息的概览浮在最顶端,发送人是“江寻”。她没有点开,指尖往下一划,看到了一个未接视频,来自喻梦之,时间显示在一个小时前。
她拨了回去。
几乎是秒接,屏幕里立刻晃出喻梦之那张画着烟熏妆的脸,背景音乐吵得人耳朵疼。
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!”喻梦之的声音穿透鼓点,劈头盖脸地砸过来,“昨天晚上,怎么回事?”
调酒师嘴快,她猜得到。这下罪证确凿,想糊弄过去都没机会。
喻梦之还在拷问:“一米八几?穿得人模人样?开一不便宜的SUV?说吧,是不是江寻?”
“是。”沉知周放弃抵抗。
屏幕那头的喻梦之表情瞬间就变了,像侦探嗅到了关键线索,凑近了镜头,压低声音,“那之后呢?他把你送回家了?”
“嗯。”虽然回的是他家。
“……就回家了?没下文了?”
“有。”
沉知周的坦诚让喻梦之噎了一下。盘问的节奏被打乱,她咳了一声,才重新组织起攻势,“有什么下文?从实招来!”
沉知周看着屏幕里那个正义凛然、非要刨根问底的好友,沉默了两秒,然后,她给了那个最简短也最惊世骇俗的回答。
“睡了。”
对面喧闹的音乐似乎都静止了。过了一会儿,视频画面剧烈地晃动了几下,喻梦之像是在找安静的角落,再次出现时,身后变成了一堵粗糙的砖墙。
“……你们这就算复合了?”
“没。”
“没复合……没复合你就跟人上床?”喻梦之被这干脆利落的坦白给噎住,“那算什么?一夜情?看不出啊沉知周,你看着一本正经,玩得还挺野。”
沉知周笑了笑,没说话。
她想。如果这位见惯风月的女律师要是知晓,当初她与江寻情窦处开的年月,许多性启蒙的实践,其实都是自己起的头,会不会吓掉下巴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